成都拓扑学与斑斓志
城市的历史与历史的城市,就犹如谜面与谜底的关系。
谜面总是安静的,是所指,是待兔之株;而谜底却是暗流潮涌,是能指,是万千种可能在与谜面的反复对位过程中,展示出独一的适应性。反过来说,城市与历史的组合的锁钥,总有其独特的质地与凸凹。
成都市介于东经102°54′—104°53′、北纬30°05′—31°26′之间。四川盆地有一个神奇之处:这一深处内陆腹地之地,竟是海洋性气候。许多滨海的地方却是大陆性气候,甚至上海都不能算作海洋性气候。无论是看年气温变化——年较差,还是看日气温变化——日较差,被青藏高原的连绵群山呵护的四川盆地均是海洋性气候。因为这里不仅年气温变化小,而且一日之中昼夜气温变化也小,昼凉夜暖。因“华西雨屏带”的特殊原因,成都平原及周边动植物种类繁多。据《成都市志·地理志》统计,成都平原共有脊椎动物578种,兽类112种,鸟类384种,两栖类24种,爬行类29种……是许多动植物的“避难所”。由此形成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格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伴随大地隆起,四川盆地由海盆先是变成了海湾,接着变成了湖盆,这个湖盆比如今的四川盆地面积要大得多,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湖,后来地形继续抬升,盆地的边缘隆起一些高山,最后形成陆盆。成都平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足;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土壤肥沃;水系发达、河渠交错,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丰富,为成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城市发展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也决定了成都平原生物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要大大高于别的地区。比如,成都是世界海拔落差最大的城市,也是全世界唯一能在市区里见到海拔6000米以上雪峰的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成都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明的发源地。作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始源地之一,拥有璀璨而续接的城市发展史,使成都文化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在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成都是中国唯一的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城市中心未移的历史文化名城,放之于世界城市史也非常罕有;成都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的发现地;成都平原是全世界最早人工栽培茶叶、最早拥有茶叶交易市场的地区;成都是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所在地,无坝引水、自流灌溉系统哺育了天府之国,运行至今润泽近千万亩沃土,成为世界古代水利史上“道法自然”的伟大创举;成都是地方官学的起源地,西汉蜀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成为全国文庙和地方官办学府的肇始;成都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祥地,至今仍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道教重镇之一;成都是地方志的故乡,西晋崇州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也是历代修志的榜样;成都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诞生地,在世界货币史上留下了第一道强力的划痕……
对此,巴蜀学者童恩正有一段论述:“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里,古蜀世界浪漫而神秘。历史学家谭继和认为它具有下列文化特征:“仙源在蜀”“道源在蜀”“文宗在蜀”“才女在蜀”“易学在蜀”。
巴蜀史学者林向教授讲述过这样的观点:四川盆地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起着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的“水库效应”。
在古代中原的眼界里,蜀地属于坤地。宋朝的蜀人就以为:“《易》以西南为坤位,而吾蜀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这是指一切土、一切地,以及与土地具有共性的一切事物生发的气韵走向,也暗示了蜀地厚重、绵扎、柔韧、博物、文采勃发的厚土气质。
1944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在成都锦江之滨生活一年后,写下了散文名篇《外东消夏录》,其中指出:“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
这个说法,渊源有自。
史学界普遍认为,城墙、宫殿以及武器的出现,既是国家政权出现的标志,也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当然,也可以把城市、文字、冶金作为文明的三大要素。作为古蜀文明的起源地,成都平原在秦代初期已经崛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三座都市,出现了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加之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高超的玉器手工业,在当时无疑已处于灿烂的文明时期。但是,此一阶段的文明远不是巴蜀文明的源头。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证明,在成都平原广阔的地域内,石器时代孕生的巴蜀文化,不但在华夏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历史中也有它不可忽略的重量。
成都的城市文明史长达4500年以上。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观点,古蜀文明的起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时代。概略而论,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的都邑文化的最早根据地,体现了鲜明的古蜀城邦文化特征,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上的空白。如果说宝墩文化所涵盖的6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证实成都早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就已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那么位于平原腹地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了古蜀城邦国家完成建构的辉煌阶段。这对于后人了解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都是弥足珍贵的“岁华纪丽谱”。
一个城市别称越多,就越发昭示了它跌宕的多面性。很多人清楚历史上成都一地有几个充满诗意的别称,梦郭、陆海、龟城、蜀都、芙蓉城、锦城、锦官城等,均与城市兴盛、地望有关。但纵观成都2300余年的城市发展史,其布局特点是“龟城走向、二江环抱、三城相套”,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汉代至唐代的“二江珥市”格局;晚唐至清末的“二江抱城”格局;现在的“江环城中”的公园城市格局。
易中天先生《读城记》里有一组对比:北京是“城”,广州是“市”,上海是“滩”,厦门是“岛”,武汉是“镇”,成都是“府”。“也许,这就是成都了:朴野而又儒雅。这就是成都人了:悠闲而又洒脱。因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远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马乱,却又享受着华夏的文化福泽。那崇山,那峻岭,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没有阻隔它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也没有使它变得褊狭怪异,只不过护卫着它,使它少受了许多磨难少吃了许多苦头。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温柔滋润的气候,则养育了一群美滋滋乐呵呵的成都人……
在我看来,这一切特征的根性,在于成都彰显出越来越清晰的“城市韧性”。
要详细梳理古蜀文明的演变以及成都的城市、风俗变迁,我把目光集中在城市的沧桑屋檐下,投射在它的砖石与阡陌之间,寄托于对碧水、城堞和往事的感叹中。城市是有性格的,城市同样有传承,而成都所蕴涵的骨中之钙、血中之盐,不但反映在闲适的生活节奏与建筑中,更彰显在人们的生活欲望的深处。
城市如迷宫。一座历史从未中断、从短暂衰落中可以奋然崛起的超级城市,恰如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笔下城市所具有的“拓扑学结构”。拓扑学是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学科,它只关注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如果以此观察成都,可以发现2500多年来,无论成都遭受了怎样的战争洗礼与移民入川,城市的诗意底蕴从未改变。
我认为,城市的最高境界是“诗意城市”,而韧性城市与诗意城市并不矛盾。所谓的诗意城市,用通俗的语言讲就是“这个城市谁看了都愿意去品味它,因为它与众不同,它有独特的魅力,有独特的美感与诗意,有让人羡慕的地方”,诗的想象与诗的生活。诗歌并不是非要写在纸上,诗更多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唯有将纸上之诗与生活之诗彻底交融,方为成都独有的城市魅力。
战国末年秦统一巴蜀,置巴郡和蜀郡。秦汉建立蜀郡、益州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的“华”,指的是秦地方言。而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移民入川,如今的四川方言就是在湖北官话基础上形成的,使四川方言具有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源远流长的继承性。
而四川最为流行的两个方言词是:安逸与巴适。
通过史料分析,可以发现“安逸”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至乐》中:“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口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这其中的”安逸”即为安闲、舒适之意,在之后的文献中也表相似意义。蜀人具有幽默的天性,其口语里的“安逸”,含有褒义、贬义、中性等含义。也就是说,这是源自北方最后成为的蜀方言。
而“巴适”明显是巴地方言。“巴食”,有斜靠着身体吃东西的本意。逐渐发展为:一是指很好、舒服、合适;二指正宗、地道。通常表字为“巴适”,也有表“巴食”。
在后工业化的氛围中,我们开始考虑一种人文的追问——人到底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或者说什么样的城市更适合于人生存?丰厚的历史对城市未来格局是否具有积极影响?虽然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城市在经济潮汐中不断变换的姿态,但需要铭记的是——昨天,是蜀文化的辉煌史程;今天,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实际上,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们,面对悠远历史所表现出来的谦逊之感,来源于一种更深层、更强有力的感受。正如朱自清先生所感受到的那样:“成都春天常有毛毛雨,而成都花多,爱花的人家也多,毛毛雨的春天倒正是养花天气。那时节真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路相当好,有点泥滑滑,却不至于‘行不得也哥哥’。缓缓地走着,呼吸着新鲜而润泽的空气,叫人闲到心里,骨头里。若是在庭园中踱着,时而看见一些落花,静静地飘在微尘里,贴在软地上,那更闲得没有影儿……”
原始的“蜀”字,是一个象形字。它的上部为皿,就是“竖目”的意思。所谓“纵目”,指的是在两眼之间的额头正中,还有一个纵立的眼睛。诗意地说,张开了“第三只眼睛”。《荀子·赋篇》:“以能合纵”。“纵,竖也。”所谓竖目,就是纵目。蜀字上为人首,而中纵一目,下身为蛇。那么我们可以打量蜀的结构三部曲:蛇(龙)身、人首、纵目,由此构成了古蜀族的图腾。有学者认为,这一图腾所指,恰是颛顼之孙——火神祝融。
置身于三星堆遗址低缓而宽大的祭祀土台上,“有时白云起,天地自卷舒”。我想起当地民间对这一带的称呼:宽山。“纵目郊原乱絮飞,好风娇叶弄天机。”我们纵目古今,成都街道的主角不是房屋、公园、绿道、植被和车流,而是生生不息的人民。
司马相如的一句话,深刻概述了成都的非凡气质:“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凡的人置身当下的时代,必将创造跨越过往的辉煌之功。(蒋蓝)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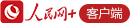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